2022江西紡織服裝周暨江西(贛州)紡織服裝產業博覽會隆重舉行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一中...
當地傈僳族獵人描述,
他們是如何一頭頭地追獵蘇門答臘犀牛,
直到一頭也不剩。
獵人說:“都沒了,
已經好多年沒看到半頭犀牛了。

蘇門答臘犀牛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動物,極端害羞且行蹤隱秘。它們也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生物之一,被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簡稱IUCN)的紅皮書列為“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生物。就在我和艾美見面的那個黃昏,它們的總數可能還不到400頭,而且之后數量仍不斷下降。如今,在我寫作本書的2001年,它們只剩下差不多300頭了,其中17頭為人工飼養。這種動物可能沒有幾十年可活了。至少有一位專家,托馬斯·福斯(Thomas Foose),認為它們只有50%的概率能活到21世紀中葉。
在野生動物學家與環境保護生物學家的眼中,蘇門答臘犀牛是一種傳奇動物。許多到它們產地森林中尋找芳蹤的人,幾乎連驚鴻一瞥都難。這些人通常只能寄望在河邊或山脊上,找到它們打過滾的泥坑和足印。運氣好一點的人,也許可以聽見它們在樹叢中行走的沙沙聲,或是嗅到空氣中飄蕩的一抹特有的味道。至于我,永遠也享受不到這種經歷。但是相反,我很懷念艾美,并將一小撮蘇門答臘犀牛的毛發放在書桌上,作為蘇門答臘犀牛以及所有消失中的生物留給我的護身符。
蘇門答臘犀牛的另一項特別之處在于,它們是活化石。它們的屬最早可以推到漸新世,起碼是3000萬年之前(相當于追溯至恐龍年代的一半時間),使得它們成為除了幾種熱帶蝙蝠之外,世界上最古老、幾乎沒什么改變的哺乳類動物。我忍不住想起,那個遇見艾美的黃昏是多么不凡,且令人震驚,我竟然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可能是它們在地質年代中存在的最后一刻,觸摸到這種神奇的動物。
走向滅絕的犀牛

犀牛曾經是地球上的統治者之一。在人類出現前數千萬年,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犀牛,從像河馬般的小犀牛,到比大象還大的巨犀牛,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森林與草原中,是大型草食性動物的優勢種。蘇門答臘犀牛是5種存活下來的犀牛之一。它們是亞洲有兩個角的犀牛。比蘇門答臘犀牛更罕見的爪哇犀牛,則只有一個角。爪哇犀牛的近親,體型較大的印度犀牛也是只有一個角,它們是世上體型第三大的陸地動物(僅次于非洲象及亞洲象),數量還算足夠多,全球約有2500頭,因此被環保生物學家列為“瀕危”(endangered)而非“極度瀕危”生物。
黑犀牛和白犀牛僅見于非洲撒哈拉沙漠周邊,和蘇門答臘犀牛一樣,也有兩個角,但是它們和蘇門答臘犀牛很不相同,而且它們兩者間也很不同。不過,它們也已成為瀕危生物,處境岌岌可危。
就解剖構造來看,蘇門答臘犀牛是5種現存犀牛中最特殊的。雖然體型最小,成獸只有約1000公斤,但相對于其他動物還是很大。它具有一項其他犀牛所沒有、遠古犀牛始祖才有的特征:身上披著茸茸毛發。剛出生時毛發黑短、脆弱,青年期時毛發變長、鬈曲,呈紅棕色,最后到了老年期又變成稀稀落落,短而硬,呈黑色。一般人很不習慣見到長著毛發的犀牛,主要是因為蘇門答臘犀牛太少見了,是一本活生生的博物學教科書。
蘇門答臘犀牛的獨特之處還在于它們最適合生活在有很多穩定水源的山地雨林中。它們是強有力且敏捷的爬山專家,被追急了,可以沖過矮樹叢,在陡坡上上上下下。它們也有辦法輕易渡過河或湖泊,有些甚至被人撞見在大海中向著外海游起狗刨來。白天,它們到處閑逛,在泥坑或池塘中打滾,一方面是為了涼快,另一方面則是讓體表的泥巴保護自己不受可惡的牛虻、馬蠅的攻擊,因為亞洲的低地森林盛產牛虻、馬蠅。
到了晚上,蘇門答臘犀牛會在成熟的樹林下覓食,在樹木傾倒的空地及河濱,吃食更鮮嫩多汁的小樹苗及灌叢。它們會一邊踩踏植物,一邊用那粗短的角來折斷矮樹枝,以便多吃些。從泥坑到主要的覓食地,往往已踩出一條明顯的路徑。另外,蘇門答臘犀牛也會不時造訪鹽堿地,以攝取生存上不可或缺的礦物質。身為草食性動物的它們,除非被激怒,一般并不兇猛:只有在自我防衛、保護幼獸,或驅逐入侵領域的其他犀牛時,才會發動攻擊。
除了偶一為之的交配,以及雌犀牛照顧幼仔外,蘇門答臘犀牛平常都是獨來獨往的。正常情況下,幾乎看不到它們的蹤影,每一頭成年犀牛的領地約為10到30平方公里,只有當領地糧草用罄時,它們才會轉換泥坑及覓食地點。雌犀牛一胎只生一頭,然后帶在身邊照顧3年。之后,它們便會將小犀牛趕走,讓小犀牛去找尋自己的領地。人工飼養的蘇門答臘犀牛,最高壽命紀錄為47歲。然而,由于人類盜獵猖獗,如今野外可能難有高壽犀牛了。
蘇門答臘犀牛族群的衰減,是漸進且不知不覺的,并非突然發生的慘案,如果用疾病來比喻,比較接近癌癥,而不像心臟病突發。它的衰減模式是最典型的物種消失模式。根據歷史記載,蘇門答臘犀牛原本分布在極廣大的森林地區,從印度經緬甸到越南,然后往南達到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及婆羅洲。100萬年或更久以前,當腦容量較小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從大陸西部及中部,擴張到地處熱帶的東南亞時,對它們必定不陌生。這些人類老祖先大概也會試著捕獵蘇門答臘犀牛,只憑著他們粗陋的工具,以及犀牛棲身的樹林難以穿越,得手機會恐怕不大。也正由于蘇門答臘犀牛的神出鬼沒以及野生棲息地的保護,它們在各地都維持著相當大的數量,甚至到人類開始有歷史記載的年代,都是如此。有人計算過,在蘇門答臘北部的古南路沙國家公園(Gunung Leuser National Park)的鹽堿地中,它們的密度曾經高達每平方公里14頭。
到了1980年代中期,這種密度幾乎是完全不存在了。整個族群的數量降到500至900頭,包括人工飼養的16頭在內。北方族群只剩下6或7頭,而且地點僅限于緬甸。至于其他地區,馬來半島約有100頭,婆羅洲30到50頭,蘇門答臘400到700頭。目前,它們的數量還在繼續下降中。緬甸那一支顯然已經滅絕了,婆羅洲的很有可能即將步其后塵。看來,不出幾十年,它們在野外勢必完全絕跡,除非現在能來個趨勢大逆轉。
搶救行動
蘇門答臘犀牛是因為垂垂老矣而死嗎?難道它們的時辰到了,就像我們壽終正寢的大姨媽克拉麗莎(Great Aunt Clarissa),我們理應放手讓它們安息嗎?
不,完全錯誤,絕對不是這么回事。斷了這個念頭吧!這個想法真是錯得離譜。蘇門答臘犀牛正如許多典型的絕種生物,都是英年早逝,至少在生理層面是如此。認為這種動物已走完自然生命周期,是基于一種錯誤的類推上。瀕危動物并不像垂危的病人,延長壽命需要付出的看顧費用太過昂貴,而且沒有多大益處。事實恰恰相反。大部分稀有且數量衰減中的動物,其族群都是由年輕、健康的個體所組成。它們只不過需要時間和空間來成長,以繁衍被人類活動所剝奪掉的族群。
加州禿鷲(Gymnogyps californianus)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89作為世界最大的飛鳥之一,加州禿鷲在北美洲曾經廣泛分布,而后來卻接近絕種邊緣,但這并不是因為它們的遺傳出了問題,而是因為人類摧毀了它們大部分的天然棲息地,而且還對那些幸存者大肆捕獵、毒殺。最后,當野外只剩下12只禿鷲時,生物學家把它們捉來,和圣迭戈附近一個人工飼育族群安置在一塊兒。經過悉心保護和喂食干凈食物,這個混合族群一下子就繁衍起來。有幾只最近被野放回大峽谷(Grand Canyon)以及其他特定的原居住地點。

加州禿鷲起碼需要好一陣子(我們衷心希望未來能持續幾千年),才能再度成為能夠自由自在生存的動物。如果能在它們以前的繁殖區域內重建棲息地,而且不再受外界干擾,那么加州禿鷲就有可能再次展開2.7米寬的翅膀,翱翔于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的上空。當然,短期內這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但是,在美國的動物群中備受注目的加州禿鷲又獲得了重生。
其他趕在最后一刻進行的搶救行動,也證實了瀕危物種通常與生俱有的彈性。最戲劇性的例子要算是毛里求斯隼(Mauritian kestrel)。90這種小型鷹類只出現在印度洋的島嶼毛里求斯島上,它們在1974年時,只剩下一對籠養的雌雄鳥。大部分環境保護人士都放棄它們了。然而,鳥類孵育專家瓊斯(Carl Jones)和他同事的一場壯舉,卻把這個族群搶救了回來。
現在已有將近200對鳥,一部分人工飼育,一部分被野放,總數可能是人類定居毛里求斯時的半數。這場瀕臨死亡的經歷,迫使該族群通過一道生存瓶頸,將毛里求斯隼原有的基因多樣性都失去了,好在現存基因中的缺陷,并沒有達到會損害它們生存或繁殖能力的程度。
由于這種終極搶救行動非常昂貴且費時間,它們只能用于數千種瀕危動植物中的一小部分。而這些少數的幸運兒,通常都是比較大型、美麗且富有吸引力的物種。
不過,并非所有人工飼育計劃都能成功。很不幸,蘇門答臘犀牛的前景尤其不被看好。這種動物是世界上最難繁殖的大型哺乳類動物,困難度甚至超過大熊貓。主要障礙包括雌獸排卵期極短、排卵需要雄犀牛刺激,以及由于個性孤僻,不交配時會對潛在配偶有強烈的攻擊性。17頭飼養在動物園或雨林保護區的蘇門答臘犀牛中,只有3頭雄犀和5頭雌犀有過交配行為。但是在這5頭雌犀中,只有辛辛那提動物園的艾美受孕成功。令保護學家們興奮的是,在連續好幾胎都流產之后,艾美終于在2001年9月13日生下一頭健康的小雄犀。
不堪負荷的盜獵壓力
造成蘇門答臘犀牛在野外數量銳減的原因都很清楚,但是到目前為止難以阻擋這種趨勢。原本濃密得寸步難行的亞洲熱帶森林,被人類以驚人的速度砍伐殆盡,之后漸漸被農田和油棕櫚所取代。然而,單單是棲息地的大量破壞,并不見得會對蘇門答臘犀牛造成致命傷害。分布在蘇門答臘、婆羅洲以及馬來半島上的自然保護區,面積還是足夠養活一小群犀牛的。
真正致命的壓力在于盜獵,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盜獵足以在幾年內消滅這個物種。驅動盜獵的主因是傳統醫藥的大量需求,因為有人相信(雖然沒有什么依據),犀牛角能治療許多疾病,從發燒、喉炎,一直醫到腰痛。結果卻幫蘇門答臘犀牛鋪成一條通往死亡的市場經濟惡性循環之路。當犀牛日益稀少,犀牛角價格便升高,使得盜獵更為猖狂,于是犀牛角變得更稀少,價格也就更昂貴了。1998年,非洲黑犀牛角叫價攀升到1公斤1.2萬美元,與金價差不多,而體型更大的印度犀牛角,每公斤價格更是高達4.5萬美元的天價。我不清楚蘇門答臘犀牛角價格為多少,但我認為它可能和體型較大的印度犀牛同價位。
1970年代全面非法獵殺犀牛的速度增快,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實施石油禁運造成的意外結果。當石油價格攀升,阿拉伯國家的人民收入也跟著增加。受惠者中,包括來自窮國也門的年輕人,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工作,想多賺點錢。如今,他們買得起更昂貴的阿拉伯腰刀,這種腰刀是也門當地慶祝成年禮的必備物品。由于最上等的腰刀刀柄是用犀牛角制成,盜獵犀牛的風氣也因此興盛。
傳統醫藥加上刀柄的需求,盜獵犀牛的行為一下子暴增,摧毀了世界各地的犀牛族群,情況嚴重得從前做夢都想不到。1909到1910年,美國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91曾率領他的非洲探險隊,從肯尼亞的蒙巴薩(Mombasa)深入內陸,當時黑犀牛約有100萬頭。美國這位偉大的環保總統也良心甚安地獵殺了幾頭。到了1970年,黑犀牛還保持在6.5萬頭左右,但是隨后由于阿拉伯腰刀的熱潮而遭殃,1980年,只剩下1.5萬頭左右,1985年,更是銳減到4800頭。15年后,即2000年,只剩下2400頭黑犀牛了。1997年,也門終于成為《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稱CITES)82的一員,如此或許可以緩和犀牛角的需求量。但是在亞洲,傳統醫藥對犀牛角的需求量仍然居高不下,高得足以讓蘇門答臘犀牛滅種。
獵捕壓力會愈來愈大:盜獵者只要獵到一頭犀牛,就可以賺到相當于10年的薪資,難怪他們愿意甘冒坐牢甚至送命的危險去獵殺犀牛。不幸的是,對蘇門答臘犀牛來說,在茂密的亞洲熱帶雨林中,盜獵者承受的風險其實并不很大,在那兒,它們無聲無息地被獵殺,然后再無聲無息地消失。
早年犀牛角價格還沒有這么高,當地獵人只有在發現蘇門答臘犀牛的新足跡時,才會獵殺它們,比較看機會來行事,并不會特別要獵殺某一種動物。然而自從犀牛角價格飛漲,以前業余的獵人變成了專業的捕獵者,在森林中到處搜尋犀牛蹤跡。他們會設計許多機關來誘捕犀牛,例如偽裝的陷阱,或在犀牛路過的地方懸掛削尖的木棒,只要引線一觸動就會掉下來插住它們。接著,獵人迅速以來復槍解決這些無助的動物,分割它們的肉,切下它們的角,然后轉交給待命中的經紀人去運銷。這出悲劇的結局不難預料:400人的野炊以及零售犀牛角所得的500萬美元的收入,鋪就了蘇門答臘犀牛最后的滅絕之路。
拯救蘇門答臘犀牛

1992年9月,著名的亞洲大型哺乳類動物專家拉賓諾維奇(Alan Rabinowitz),率領一支探險隊前往婆羅洲最北端,進入沙巴州的達隆河谷(Danum Valley),去尋找最后的蘇門答臘犀牛。達隆河谷已規劃為野生動植物保護區,一般認為應該有比較多的蘇門答臘犀牛,盡管它們的族群在這座大島上已經日益減少。探險隊分為五支小隊,三支以步行方式進入森林,兩支則乘直升機抵達其中心位置。每一支小隊都以不同路徑來回穿越河谷。全部加總后,他們最多只找到7頭犀牛。他們也看到被遺棄許久的泥坑和所謂的犀牛“鬼魂腳印”(ghost spoor),也就是已經死亡的犀牛所留下的痕跡。此外,他們還撞見過盜獵者。有一次,一支直升機小組幾乎意外地降落到一群盜獵者的營地上,嚇得他們一哄而散。
緬甸在20年前設立的塔曼蒂(Tamanthi)禁獵區,這個地區是為了保護老虎、蘇門答臘犀牛以及其他大型本土哺乳類動物而設置的。結果還有為數不多的老虎,但是完全看不到犀牛的蹤跡。當地傈僳族獵人描述了他們是如何一頭頭地追獵這種動物的,直到一頭也不剩。獵人們說:“都沒了,已經好多年沒看到半頭犀牛了。”其中幾個年紀較大的人還記得最后一頭犀牛被獵殺、宰割、取角的情景。
蘇門答臘犀牛是否可能像加州禿鷲和毛里求斯隼一樣,被及時搶救出墳墓呢?兩項標準搶救方法中,人工飼育到目前為止沒什么成效,而現存保護區在防止盜獵方面,成績也不理想。致力于解決這個問題的幾位犀牛專家,都認為蘇門答臘犀牛已經步上窮途末路。他們指出,不論是什么解決方案,現在不做將永遠沒有機會。
另一個新的拯救方法是,在雨林地區用圍籬圈起一塊面積介于動物園和保護區之間的禁獵區,然后嚴密監控。這類設施面積差不多100英畝,已經在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以及沙巴設立了。到目前為止,這些地方還是沒辦法成功復育犀牛寶寶,但起碼它們是處于半天然的情況,也許還有益于犀牛繁殖。同時,既然情況如此瘋狂(犀牛角的天價、缺乏科學證據的療效以及因此造成的嚴重環境破壞),最有希望的辦法是,看看能不能用什么法子,說服或強迫醫生把犀牛角從藥典中除名。
擋不住的市場力量
對于這類事情,西方工業國的所謂道義雖然不難體會,但是不見得合理。同樣無法約束的市場力量,在世界各地所有國家都一樣暢行無阻。500年來,位于克什米爾的斯利那加城(Srinagar)里,織工們都在處理藏羚羊(Tibetan antelope)93的羊絨,它們的質量之佳,在波斯語中贏得“沙圖什”(shahtoosh)的稱號,意思是“羊毛之王”。
到了1980年代末,全世界忽然風靡起沙圖什披肩來,一些名流,譬如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以及名模布里克利(Christie Brinkley),都曾一派天真地披掛這種披肩。市場需求量立刻激增,由每年數百件增加到數千件。單件披肩的價格也飆漲到1.7萬美元。很自然,獵人就開始無情地追捕藏羚羊,以求獲得更多羊絨。制作一條1.8米長的圍巾,需要三只以上的藏羚羊,如今,沙圖什在克什米爾依舊能合法買賣,據估計每年約需獵殺2萬頭藏羚羊。目前野外只剩下約7.5萬頭,大部分都位于遙遠的青藏高原西部或是中北部。
美國也是一樣,加利福尼亞州沿岸對于鮑魚的需求量之大,使得四種淺海鮑魚因商業捕撈而數量下跌。(我也是一不小心成了鮑魚的消費者。)缺貨之后,焦點又轉到了白鮑魚身上,這是一種產于深海、比較不易取得的鮑魚,同時也是最柔軟和最受歡迎的品種。從那以后,1969—1977年間,白鮑魚捕撈量激增,最后使它們的數量減少到瀕危滅絕的程度。今天,盜捕依然猖狂,白鮑魚終于完全消失了。
一百心跳俱樂部
蘇門答臘犀牛以及白鮑魚是教科書的最佳范例,見證了人類如何借由野蠻濫捕及其他活動,將世界各地大批物種逼到只差一步就要淪為環境保護科學家口中的“全球”滅絕狀態,也就是全球都找不到存活的該種生物了。最危險的一群動物,我稱它們為“一百心跳俱樂部”(Hundred Heartbeat Club),是由存活個體數小于或等于100的動物組成,因為它們距離全球滅絕只有100下心跳。這里面很搶眼的動物包括菲律賓鷹、夏威夷烏鴉、藍金剛鸚鵡、白鰭豚、爪哇犀牛、海南長臂猿、溫哥華島土撥鼠、得克薩斯州尖嘴魚以及印度洋腔棘魚等。其他排隊等著提早加入一百心跳俱樂部的動物,則有大熊貓、山地大猩猩、蘇門答臘猩猩、蘇門答臘犀牛、金竹狐猴、地中海僧海豹、菲律賓鱷以及北大西洋最大的魚類倉門鰩。
全球10萬種已知的樹種中,至少有976種處境同樣危急。94有一群狀況極度危急,環保專家稱它們為“活的死物”(living dead):其中有三種植物只剩下一棵植株,其中就包括中國的普陀鵝耳櫪(Carpinus putoensis);另外還有三種植物只剩下三到四棵植株,如夏威夷美麗的木槿(Hibiscus clayi)。
至于單一地區瀕危植物密度最高的紀錄,可能要歸于胡安費爾南德斯群島(Juan Fernández Islands),這個群島距離智利海岸600公里遠,素以塞爾扣克[Alexander Selkirk,他的事跡被笛福(Daniel Defoe)改寫成小說《魯賓孫漂流記》,于1719年出版]的隱居地著稱。在這塊180多平方公里的陸地上,共有125種別處沒有的植物。
然而,幾世紀以來,由于游客、居民、火災、濫伐以及人們帶來的羊群的啃食,使得當地20種特有植物的野外個體僅剩下25株甚至更少。其中有6種小樹為當地獨有的Dendroseris屬。里面有一種學名叫作Dendroseris macracantha的植物,公認只剩下一株了,生長在某座花園中。1980年代,這棵植株不小心被人砍了,于是這種植物也被認定從世界上消失了——直到后來有位當地導游在陡峭的火山脊內側發現了另一棵植株,才又有了的幸存者。還有一種胡安費爾南德斯群島特有的檀香木,據信也已經絕種,但是仍然懸著一線希望,或許將來又能找到一兩株。
可想而知,許許多多物種都正從極度瀕危走向“活的死物”,最后被人遺忘。雖然有些作家(當中沒有一位是生物學家)懷疑,是否真有大量物種絕跡。他們會這樣想,也許是誤以為物種滅絕就如同個人的死亡般,很少有人親眼看見。事實上,由于瀕危生物極端罕見,光是要找出它們的生長地點就很困難了。從統計學上來講,瀕危生物在那種危險的狀態下只會停留一下子。每天都有幾種生物屬于“極度瀕危”的紅色警戒區,還有更多生物僅僅被列為“瀕危”物種,或是列入稍微令人放心的“易危”(vulnerable)物種。這種情況,就好比特護病房的病人在醫院里總是占少數:因為只要有一點兒閃失,他們就死了。
最近許多物種滅絕無疑都被忽視了,因為有些物種實在太稀少,還來不及被人發現、命名,就消失無蹤了。在環保生物學上,有一個著名案例,那就是夏威夷的毛里求斯島蜜雀(po‘ouli),這種鳥體形和鶯類相仿,由于太過特殊,在分類上自成一屬,屬名叫毛里求斯島蜜雀屬,有一陣子它們只剩下化石標本,因此被認定早在美國殖民者上岸前就絕跡了。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期,有人又在一處與世隔絕的山谷森林中,發現一小群活生生的毛里求斯島蜜雀。然而,20年后,它們的數量更少了,即使在這塊最后的堡壘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稀稀落落的幾只。這種鳥可能很快就會絕種(如果現在還沒有),而這一次,將是千真萬確地消失了。
其他不像鳥類這么惹人注意的生物,例如無數的真菌、昆蟲以及魚類,類似的劇情上演了千百遍,卻沒有留下任何記錄顯示它們曾經存在過。
澳大利亞生物大屠殺
只有人們研究最多的動植物,才可能觀察和計算出其被屠殺的程度。譬如,在263種澳大利亞原產哺乳類動物中,有16種已知是在歐洲殖民者抵達后消失的。96以下是這種物種的具體名單,括號里的數字是它們最后被人看見的時間:達令草地跳鼠(1740年代)、白足樹鼠(1840年代)、大耳跳鼠(1843年)、寬臉小袋鼠(1875年)、東部兔袋鼠(1890年)、短尾跳鼠(1894年)、愛麗斯泉鼠(1895年)、長尾跳鼠(1901年)、豚尾袋鼠(1920年)、格氏袋鼠(1927年)、沙漠袋貍(1931年)、小袋貍(1931年)、中部兔袋鼠(1931年)、小巢鼠(1933年)、袋狼(1933年)、圓尾兔袋鼠(1964年)。
很可能還有一些更罕見、更不顯眼的澳大利亞動物,雖然在19世紀初仍然存在,但是還沒來得及引起博物學家的注意就消失了。不僅如此,1996年,又有34種動物(占澳大利亞現存哺乳類動物的14%)被IUCN列入紅皮書,處境從易危、瀕危到極度瀕危不等。
澳大利亞生物的大滅絕并非始于西方文明入侵之時。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澳大利亞哺乳類動物的巨大變動,其實只是當地動物群漫長衰亡史中的最后一幕。6萬年前,在澳大利亞土著上岸之前,這塊大陸型島嶼是許多超大型陸地動物的家園。這兒有許多不會飛行的牛頓巨鳥(Genyornis newtoni),是現代巨鳥鴯鹋在進化上的近親,只是它們的腿較短,而且體重高達80到100公斤,是后者的兩倍。此外還有一種可能以牛頓巨鳥為食的巨蜥(monitor lizard),長相類似現在印度尼西亞的科摩多巨蜥,但是體積大得和恐龍似的,長達7米。它們生活在一群巨大的動物之間,這些動物有點類似放大了的樹獺、犀牛、獅子、大袋鼠,以及有小汽車那么大、長了角的陸龜。
這個巨型動物群必定存在了數百萬年之久,但是就在批土著抵達之際,突兀地終結了。這批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類先鋒,是在5.3萬到6萬年前,從現今的印度尼西亞登上澳洲大陸的。在那之后不久,顯然時間不會超過4萬年前,巨型動物群就消失了。體型比人類大的陸棲動物,無一幸免。另外,還有許多其他哺乳類、爬行類,以及體重介于1到50公斤、不會飛的鳥類,也都絕種了。
生物學家利用同位素定年法檢測牛頓巨鳥的蛋殼碎片,測定出這種鳥是在約5萬年前一段很短的期間內,從澳洲全面滅絕。它們的絕種不能輕易歸因于氣候變化、疾病,或火山活動。不過,牛頓巨鳥消失的時間點,卻與批人類抵達的時間完全吻合。看來,等到歐洲人殖民澳洲后,在同行的老鼠、兔子和狐貍的幫助下,將物種滅絕提升到超越土著影響力的更高層次。
巨型動物的消失
毀滅生物多樣性的人類,是從食物鏈上方依序往下獵殺的。首先遭殃的動物都是體型大、反應慢而且好吃的。有一條準則可以暢行天下,那就是凡是人類足跡踏上的處女地,巨型動物群馬上就會消失。命運同樣乖舛的,還有最容易捕捉的陸鳥和陸龜。至于小型、靈巧的動物,數量雖然下降,大都能茍延殘喘。
考古學家發現,動物滅絕會發生于殖民者抵達后幾百年(最多1000年)內。馬達加斯加島的動物滅絕史可以說是教科書的經典案例。97這個坐落在非洲外海的大島,最晚在8800萬年前便已由南亞次大陸分離出來。從那以后,由于亞洲板塊往北漂移,這兩塊陸地便越離越遠。這段時間,馬達加斯加島逐漸進化出非常獨特的生物形態。2000年前,也就是印度尼西亞航海者還沒登陸前,它簡直就是一座巨獸動物園。島上的森林和草原孕育出龜殼寬達1.2米的陸龜,體積與牛相仿的侏儒河馬,一種山貓大小的獴類,以及馬達加斯加語所謂的aardvark(土豚),它們因為解剖構造太過特別,被動物學家另立為一個目,叫作馬達加斯加獸目(Bibymalagasia)。
同時,島上還有6種象鳥(elephant bird),體型大小不一,小至鴕鳥般大小,而最大的象鳥,站起來有3米高,體重有半噸,產下的蛋則有如足球大小。9世紀時在馬達加斯加北部海岸工作的阿拉伯商人,都曉得這種大鳥,消息來源可能是當地人口耳相傳,或有親身經歷的馬達加斯加人親口述說。于是,這種鳥便化身為傳奇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大鵬鳥“魯克”(roc,一種長得像鷹、能夠一把攫走大象的巨獸)。同樣神秘的還有狐猴,它們是最早的靈長類動物之一,因此可以算是人類的遠親。馬達加斯加島最初有大約50種狐猴,體型大的包括:重約27公斤、樹棲、長得像猿的狐猴;體重約50公斤的狐猴,相當于澳大利亞樹棲、專吃桉樹葉的考拉;還有另一種居住在地面、比成年雄性大猩猩還大些的狐猴,其生態區位很可能相當于新大陸里已經滅絕的陸獺。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一中...

Burberry是一個具有濃厚英倫風的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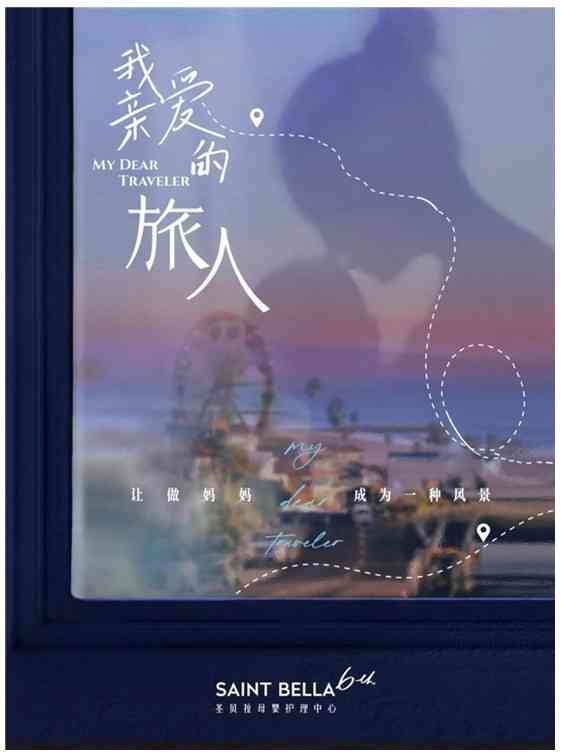
高奢月子中心圣貝拉(SAINT BELL...

近年來,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復雜多變,不確定...

如果有這樣一...

近日上海智美顏和以60后--90后的不同...
名品導購網(www.cctv-ss.com)ICP證號: 蘇ICP備2023000612號-5 網站版權所有:無錫錫游互動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2005-2023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禁止復制轉載。郵箱:mpdaogou_admin@163.com